无论写什么题材的小说,一定要遵循以小见大的写作逻辑

很多人喜欢设定宏大的背景,然后写宏大的主题,那么要怎样去表现出宏大呢?宏大的叙事应该怎么写呢?
请记住一点,没有一部宏大主题的小说,是从宏观着手的,也没有一部宏大叙事的小说,一个劲是在写大事件的。
无论是多大的事件,都需要由人去经历,让人去感受,从而对事件大小作出判断和衡量,所以,再大的事件都要通过人的视角去叙述。人物写得越细、越真实,宏大的事件才越有震憾力。
总结成一句话就是,像医生做微创手术一样,切开一个小切口,去窥探身体的大秘密,这就是本文要讲的以小见大的写作技巧。
具体怎切入呢?
一是从小人物切入。
宏大主题的落地,往往始于个体对生命、社会现象的凝视。
90 后作家王明宪在《春水流》中塑造的 “不被看见之人”,就是这一技巧的注脚,扎纸人三老猫冒着折寿风险为早夭女仔扎纸人,残疾匠人薪饭在斗牛场舍身救人……这些身陷困顿的小人物,用他们的勇气,在生存碾压的社会环境下,坚守着善良和人性的良知,从而折射出转型期社会底层的精神光谱。
还有王雨在《向死而生》中描写的脑瘫患者俞帅奇,他的剪刀步不仅丈量出康复之路,更串联起了重庆大轰炸的集体记忆、汶川救灾的时代印记,将个体苦难嵌入时代的语境,这样的故事才具有震憾力。
这种书写并非是对大历史的消解,而是让抽象的时代阵痛转化为,具体的可触摸的生命体验。
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做呢?理由是,比起宏大叙事的全景式的铺陈,小人物的悲欢更能唤醒人们共情,这种以小见大的手法,远比空洞的生命礼赞更具穿透力和感染力。
二是从小载体切入。
越是抽象的宏大主题,越需要具体的载体作为支撑点。
马伯庸《长安的荔枝》以一桩荔枝转运的差事为切入口,让小吏李善德的奔波轨迹,成为解剖唐代官僚体系的手术刀;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韩江的《素食者》中,英惠的 “植物化” 身体选择,将父权制与资本暴力的宏大批判,浓缩为皮肤生长绿叶的具象隐喻……这些从小载体切入的妙处在于,它们既是叙事线索,更是意义的容器。
三是从小场景切入。
场景的选择暗藏叙事的智慧,一个浓缩的空间往往能成为时代的切片。
老舍在《骆驼祥子》中以茶馆为切入点,从而映照出当时的整个社会,王安忆的《长恨歌》通过王琦瑶的公寓,将上海半个世纪的变迁浓缩于闺阁的日常之中,阿来的《尘埃落定》则以土司庄园的方寸之地,上演了一场制度崩塌与人性异化的大戏。
当代小说的 “小场景” 早已超越地理属性,成为社会肌理的微观剧场。什么叫于细微处见真章?它让宏大主题脱下抽象的外衣,在小人物的泪水中显影,在日常物件的纹路里刻痕,最终成就 “一粒沙中见世界” 的文学境界。
如果说宏大叙事只叙述大事件,而没有具体的人物的话,再宏大的事件我们也是感知不到的。
本文为写作营原创,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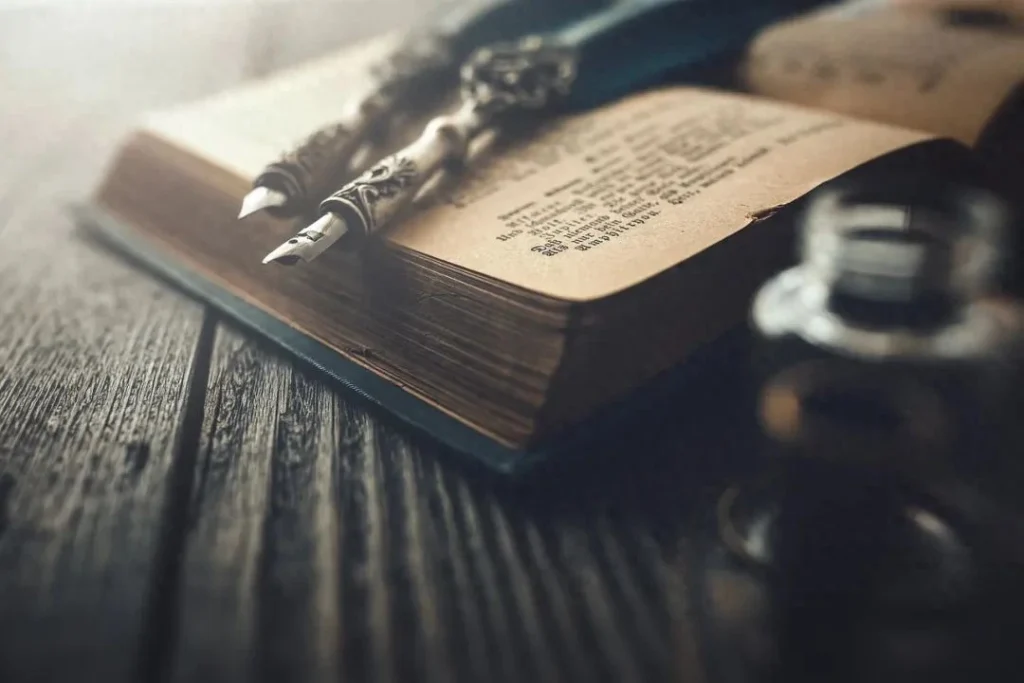
奶香芋
求推荐更多运用这种写作手法的优秀作品!想多学习学习
梦境行者
看到茶馆场景那段突然想起《茶馆》话剧,老舍先生真是用方寸之地写尽人间百态
玄铁刻
🤔话说『以小见大』和『见微知著』是同一个意思吗?感觉古人早就悟透这个道理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