写作时不可不知的 10 个核心技巧

一、“横切悬念,倒叙事件” 法
为避免叙事平铺直叙,作者可在小说开篇就设置一个统领全文的悬念,故意给读者留下疑团,以此激发阅读兴趣。1964 年 7 月 5 日《湖北日报》刊登的《一双明亮的眼睛》就巧妙运用了这一手法。
文章开篇写道:夜,墨黑,伸手不见五指。我(文中主角)要去一个生产大队,因是初次前往,路况生疏,偏偏遇上阴雨天,既无星月微光,自己又没带手电,急得团团转。就在这时,我遇到一位社员,恰好住在我要去的大队,便主动为我引路。一路上,他不时提醒:“同志,注意,前头有条沟!” 过一会儿又叮嘱:“同志,注意左边是口塘!” 最后进村时,还指着一条巷子说:“里面住着咱们队长,他会招呼你的。” 可第二天清早,我从队长屋里出来,看见一个强壮的中年人挑着桶,哼着轻快的曲子走向稻场旁的堰塘。等他走近,我猛然发现,这么一条精壮的汉子,眼睛竟然是瞎的!正诧异时,只见他从容不迫地下塘挑水。我大惊失色,急忙喊道:“…… 那是塘,小心掉下去!” 他回过头,眨了眨眼,仿佛看见了我:“你不就是昨晚我引路的同志吗?”……
读到这里,读者定会心生疑问:他真是盲人吗?为何能在黑夜中熟练引路?为何他的 “眼睛” 比常人更明亮?这便是 “横切悬念”,而作者接下来的 “倒叙事件”—— 自然会让读者忍不住继续读下去。
二、“意料之外,情理之中” 法
世界艺术大师卓别林曾说:“我总是力图以新的方法创造意想不到的东西。假如我猜到观众以为我会在街上走,那我就跳上一辆马车。”(引自《卓别林 —— 伟大的流浪汉》)这句话揭示了创作的核心:结构要巧妙,首先需 “出其不意”,但更重要的是,情节必须在情理之中。所谓情理之中,是指这种 “意外” 要与人物性格发展一致,符合客观规律和生活逻辑,既不能荒诞离奇,也不能凭空臆造,要做到曲折却合理。
美国作家欧・亨利的《麦琪的礼物》便是典范。故事讲述美国圣诞节当天,一对恩爱夫妇准备互赠礼物,都想给对方一个惊喜。妻子发现丈夫有祖传金表却没有表链,便剪掉自己最珍爱的金色长发卖掉,用换来的钱买了表链。丈夫则看到妻子有一头美丽金发却缺一套名贵梳子,便卖掉自己祖传的、格外珍爱的金表,买回一套华丽的梳子。结果两人见面时,丈夫拿着妻子送的新表链,却没了金表;妻子握着丈夫送的新梳子,长发已不复存在。夫妻俩只能相视而笑,神情凄然。这个情节虽让读者意外,却在情理之中 —— 因为他们的夫妻情深远超对 “金发”“表链” 的珍视,而在 “金钱至上” 的资本主义社会,下层小人物的命运本就充满这样的辛辣与无奈。
三、“淡化情节,形散神聚” 法
这种创作手法看似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,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,叙事平铺直叙,气氛平淡如水。但在这份平淡中,往往蕴含着直击心灵的情感;在这份淡淡的凄凉里,藏着耐人寻味的人生况味,常常达到 “无情胜有情,无声胜有声” 的效果。
张洁的《拾麦穗》便是如此。故事讲述农村一个贫苦的小姑娘,每年夏天割麦时,总会挎着篮子到收割后的麦地里拾麦穗。这时,一个卖麦芽糖的老汉会经过。别的孩子用拾来的麦穗换糖吃,唯独这个小姑娘舍不得。老汉便常常免费敲糖给她。旁人打趣说她不如嫁给老汉,小姑娘似懂非懂,老汉也不以为意,大家说笑一阵后便不再提起。可当老汉不再来卖糖时,小姑娘却独自在村头痴痴地等,一直等下去……
她在等什么?仅仅是为了老汉的糖吗?显然不是。这里面有说不清道不明的滋味,有淡淡的依恋,有普通人之间难以言说的情感共鸣…… 这便是 “形散神聚”,看似 “无结构”,实则用内在的精神线索编织出独特的情感文体。
四、“一箭双雕,一点两面” 法
小说创作中,作者如同导演,常让角色携带各种道具。优秀的 “导演” 会让道具不仅关联一个角色,而是串联起多个角色;不仅服务于一方,更让矛盾双方都与道具产生交集。通过道具,既能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,又能揭露生活本质,从而实现作者的美学表达。
当代英国作家斯丹・巴斯托的短篇《二十先令的银币》就完美诠释了这一点。文中的 “20 先令银币” 便是核心道具。作者通过这个道具,先让富有的马斯顿太太故意将银币放进一套衣服口袋,再让仆人弗斯戴克太太送衣服去洗衣店,同时交代她送洗前要掏干净口袋。弗斯戴克家境贫寒,丈夫瘫痪在床,急需用钱。这枚银币对她而言意味着太多:能给丈夫买水果、香烟,还能添一瓶酒,甚至买几件必需品…… 而马斯顿太太的真实意图,是希望弗斯戴克悄悄留下银币,之后再逼她交出 —— 以此证明穷人的 “卑劣”,反衬自己的 “高尚”。
通过这个道具,作者既展现了穷人的物质困窘,又揭露了富人的精神鄙俗,深刻揭示了当时社会人与人之间的残酷关系。小说结尾,弗斯戴克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,最终颤抖着交还了银币 —— 这枚 “二十先令的银币” 从此深深烙印在读者心中。
五、“偶然中必然,必然中偶然” 法
小说创作中,作者要善于发现生活中 “偶然藏必然” 的规律,并将其融入情节。这样的叙事既能让读者追根究底、欲罢不能,又能揭示生活中不易察觉的本质。
法国作家莫泊桑的《项链》对此技巧的运用堪称经典。小职员的妻子路瓦裁夫人为在晚会上赢得关注,向女友借来一串项链。当晚,项链配上她的美貌让她大出风头。可乐极生悲,归途上项链不慎丢失。为赔偿项链,她和丈夫不得不承受沉重的经济压力,历经十年艰辛才还清债务。然而就在债务还清时,她竟发现当初借来的项链是假的。一夜风光换来十年辛酸,片刻虚荣导致半生劳苦 —— 这一系列情节看似充满偶然,实则皆在情理之中:夫妻二人的性格、当时的社会阶层、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观念,都注定了这样的结局。
六、“银丝串珠,数点一线” 法
现代派小说家面对社会精神危机时,常以荒诞、超现实的主观想象为素材,构建看似破碎却内在统一的叙事。这类作品表面上可能是意识流式的、碎片化的,甚至晦涩难懂,但细究之下会发现,各部分之间相互关联、彼此烘托,形成 “银丝串珠,数点一线” 的整体结构。
美国作家亨利・斯莱萨的短篇《…… 以后》就以这种手法反映核战争的恐怖。小说分为 “博士”“律师”“商人”“酋长” 四个段落,看似毫无关联:
“博士” 段落中,曾出版六本《记忆学》专著的教授,在核战后失业了 —— 因为人们再也不愿回忆战争的惨状,他只能改教 “如何忘记” 的速成课程。
“律师” 段落里,核战后人口锐减 90%,男女比例变为 800∶1。过去的杀人犯本该判死刑,现在却被判处 “极刑”:与 18 个女人结婚,使妻子总数达到 31 个。
“商人” 段落中,商人本以为核战后服饰销量会暴跌,却被优生学教授告知:因原子辐射,65% 的新生儿是双头畸形,帽子等服饰需求将供不应求,他顿时松了口气。
“酋长” 段落讲述几个白人带着辐射检测仪逃到孤岛,仪器会对辐射超标者发出警报。他们与岛上土著酋长见面后,用仪器检测发现:土著人无辐射,而白人自己却触发了警报。最终土著人杀掉白人并食用其肉,也染上了辐射 —— 从此,辐射毒无处可逃。
这四个荒诞的片段,实则通过 “核战争后遗症” 这条隐线串联,共同勾勒出核战之后的社会乱象,深刻传递出对战争的恐惧与反思。
七、“明线暗线,双环连套” 法
这种技巧通过设置一明一暗两条线索,让它们平行交错、相互勾连,从不同人物、不同故事中引出深层主题。线索间既独立发展,又彼此映衬,最终共同推动主题深化。
鲁迅的《药》便是典范。明线讲述清末华老栓为给儿子小栓治痨病,清晨去买人血馒头,回家后让小栓服下,可小栓最终还是病逝。暗线则是:老栓买的是人血,来自当天被处决的革命者夏瑜,而这剂 “药” 既没治好小栓的病,也没唤醒麻木的群众。
小说结尾,小栓与夏瑜的坟墓在坟场相邻,两位母亲分别为儿子上坟 —— 明暗两线在此交汇,主题自然浮现:“愚昧的群众享用革命者的鲜血,不是医治病苦的良药;资产阶级脱离群众的革命,不是疗救中国社会的良药。”
八、“欲扬先抑” 与 “欲抑先扬” 法
“欲扬先抑” 是指对着力塑造的人物,先进行贬低或弱化,如同出拳前先收拳,这样打出时更有力量;“欲抑先扬” 则相反,先让要贬低的人物显得风光,再让其跌落,反差之下更显其本质。
马烽的《我的第一个上级》是 “欲扬先抑” 的典型。县农建局的田副局长初看时衣冠不整,披件烂棉袄,无精打采,拖沓慵懒,完全不像个领导。但在海门决堤抢险时,他却展现出惊人的魄力:熟谙全局、胸有成竹,不顾严重的关节炎,带头在风浪中搏斗,直到险情解除。前期的 “抑” 让后期的 “扬” 更具冲击力,一个鲜活的社会主义英雄形象跃然纸上。
“欲抑先扬” 在《水浒传》“武松醉打蒋门神” 中尤为明显。作者先极力渲染蒋门神的厉害,称其武艺高强、无人能敌,这是 “扬”;可武松出场后,几个回合便将他击败 —— 通过反差,既凸显了武松的勇猛,也揭露了蒋门神外强中干的本质。两种手法常交叉使用,互为补充。
九、“盆中藏月,以小见大” 法
这类小说通常题材简单、场景单一、人物不多、情节平淡,却能通过 “以小见大” 的手法,用平凡故事展现深刻主题,如同 “盆中藏月”,以一勺水映照整片星空。
叶文玲的《藤椅》便是如此:中学教师杨健领回学校发的新藤椅,全家都很高兴。可高兴过后,难题来了 —— 这个三代六口挤在 15 平方米的家里,连放一把椅子的地方都没有。最终,老杨只能惋惜地将藤椅退回学校。
故事没有传奇色彩,情节简单平淡,却深深震撼读者:解放三十年,勤恳教书的杨老师一家为何仍挤在蜗牛般的小屋里?除了 “四人帮” 的 “愚民” 政策和 “白卷大王” 的精神污染,更值得反思的是,如何清除这些余毒,让藤椅 —— 以及比藤椅更重要的尊严与幸福,真正走进普通劳动者的生活。
十、“余音绕梁,三日不绝” 法
小说的收尾至关重要。即便开头精彩、发展流畅,若结尾处理不当,也会沦为 “虎头蛇尾”。好的结尾不仅是故事的落点,更要展现作品的精髓,达到 “余音绕梁” 的效果。
结尾的关键在于:既要收束全文,又要留下回味;既要点明主题,又不能直白说教。或用一个意味深长的场景,或留一个耐人寻味的疑问,让读者在合上书后仍能反复思索 —— 这便是收尾的最高境界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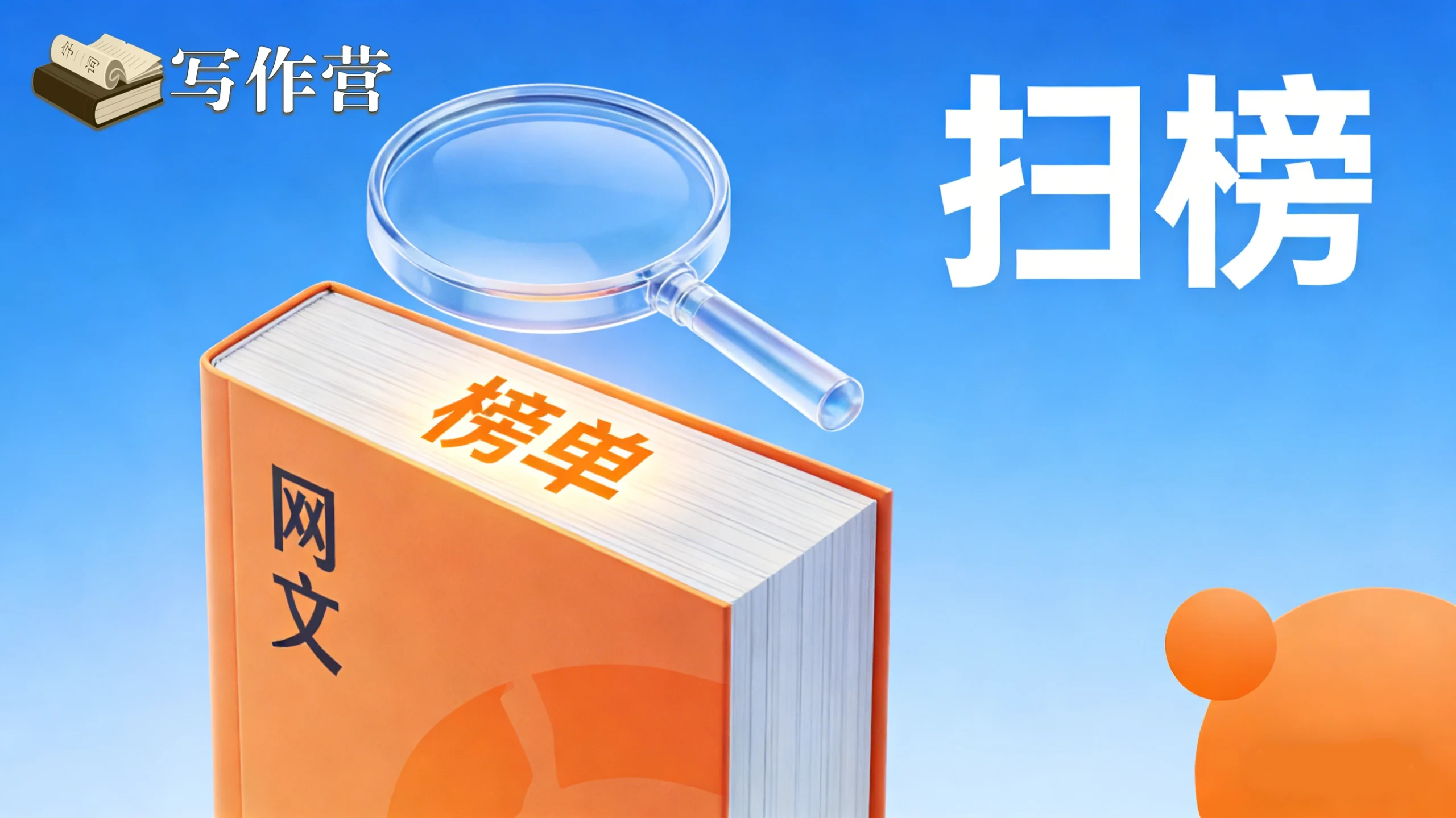


暂无评论,你要说点什么吗?